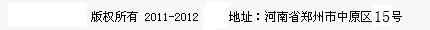月光下的出离(节选)
李燕蓉
雨的影子遮掩了整个白天,让云凌有一种错觉,似乎一睁眼已经是傍晚了。
母亲一直在忙碌,即使没有醒,云凌都知道母亲在忙碌,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其实,母亲完全可以选择在昨天、前天、上个月或者是之后的任何一天找她说这些话,但母亲似乎固执地认为,只有十八岁这一天才是她人生另一个成长的开始。她知道母亲还做了头发。每次母亲从理发店回来,除了头发上那不可思议仿佛打了蜡的地板般的光泽还有理发店特有的各种化学品混合在一起的香气。那天的空气里头发的香气完全掩盖了饭菜的浓郁,除了香气还有母亲莫名亢奋的情绪。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母亲只为那些如过江之鲫般的男人做头发,为她这还是头一次。每次母亲把男人带回家总会问她好不好?那个时候,母亲会像一头迷途小动物,期待而无助,尽管她心里完全不清楚好与不好的界限在哪里,但看到母亲突然变成一副弱小的模样,还是会害怕地点点头。母亲在做头发的那几天情绪时好时坏,不停地趴在卫生间照镜子,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望着镜子中的影像流连忘返,时而开心、时而沮丧,仿佛镜子随时可以把母亲变成另外一个人、可以变出另外一个世界来。她也试图从镜子里看出些什么,但除了自己她从未发现过任何东西。
母亲为她专门做头发这件事让当天的气氛变得异常隆重,而这份隆重对云凌而言其实是匪夷所思的。她承认,成长的确是一瞬间的事儿,仿佛推一扇门一般,推开、走过去,就不再是门里那个人,但那个瞬间究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它不是课程表也不是一个刻度会提前写在那儿。那种感觉她有过两次,一次,是同最要好的朋友,先是误解、然后不断解释,然后大家都努力保持了之前所有的亲密,包括无话不谈的氛围,尽管两个人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但只要一停下就会有大片的空隙生硬挤进来。彼此都感觉出了尴尬,却尽量避免明白这一切,直到一个下午,她清晰感觉到心底有类似树枝折断的声音,那一刻,她突然明白她们之间所有的一切、包括亲密将一去不复返了,越是解释、越是补救,补丁就会越大、越刺眼,如同徒手捞月亮的猴子,不断打捞除了溅起更多的水花,水中的月亮也会碎得更快。当时她们背后的晚霞像之前她们曾经一起度过的任何一个傍晚一样——明艳生动,她眼睁睁看着晚霞消失殆尽才拍了拍最要好朋友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去。从那天起,她明白了多数时候弥补都是徒劳的、而且毫无意义。第二次,和父亲有关。父亲在她四岁时去世,父亲的死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则新闻,从头到尾她都在场,但留在记忆里的只有混乱、哭泣和嘈杂。她一直认为对于父亲没有任何记忆,也不应该有,但是初中毕业的某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前面一个三岁的孩子摔倒的瞬间却让她心口疼了一下,父亲从记忆里嗖地跳了出来,那些一起玩耍的情景竟然就从那刻起逐渐清晰了起来,她几乎都可以感觉到父亲把她扛到肩上感觉,还有父亲的笑。记忆,原来并非书本上说的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它只是藏匿在了某个角落,因为与你久不谋面而变得模糊生疏,只要你转回头,它一直都在。
初中想起父亲的那个晚上,她问母亲,父亲是不是很爱笑?母亲愣了很久反问她:“怎么了?是不喜欢王叔叔吗?”随着母亲话音落地,她突然明白,多数时间里人与人心里的节奏都不可能在一个鼓点上,母亲过去曾不厌其烦和她谈起父亲,那时她只是自顾自地玩,没有任何感觉,此刻,当她谈起父亲,母亲却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了,对母亲而言父亲应该早已暂居在别处了吧。十八岁生日,如果一定要谈话,她也只想谈谈父亲,那个对母亲来说已经遥远了的男人。除了这个,她不认为她们有限的生活空间里还有什么是她不了解、不明白的。
……
宁远一直好奇《遇见女孩儿凌》节目里云凌和他都没有出现能播些什么,看了几期后发现可播的内容真是太多了,而一个人究竟能延伸出多少种关系、多少种话题,这个简直可以上升为一个数学问题。原来没有谁都无所谓,或者,谁都不过是一个点,只要想引申就一定能划出无数条线来,可直、可弯。栏目采访了云凌的母亲、云凌的老师、云凌的同事、云凌的老板,和云凌有关的人几乎都在栏目上露了一遍脸。云凌的母亲——向红特意做了头发,电视里的她有着美人迟暮般的风采,她还是说了那天和张警官说的话:
“我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会轻生,她一定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安静地待着。”主持人满含着热泪听她介绍云凌的过往,说到独自艰辛抚育云凌的过程向红自己也落了泪。
另一期云凌的老板说了这样一段话: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只要虔诚,你的身体就是一座庙宇,如果我们有了不安、有了恐惧,要尽早的释放出来,你要知道,除了你自己还有我、我们可以帮你。”
这段话曾被有些人批有广告之嫌,但最后还是播出了,而且出来的效果竟然不错,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平缓、自然,还配合着栏目的音乐,有些人甚至写信给栏目组说,当时听到这句话就有了治愈的作用。云凌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分别在一起回忆了不同阶段云凌的表现,无一例外,云凌在大家的记忆里都是优秀的、懂事的、乖巧的、善解人意的,别人的叙述里她像是月饼模子刻出的一枚月饼,使点劲儿就纹路清晰,轻一点就纹路模糊,除此再无其他。还有一期是云凌曾经治愈过的病人,那期镜头前特意遮挡起了茂密的文竹,透过花的缝隙只能看到说话者脸的片段,但熟悉的人应该还是可以猜出花后面的是谁,所以尽管那期节目里很多人说了很多话,有些患者甚至用低声哭泣来怀念她的好,但因为涉及某个人隐私的原因在其它时间段复播的时候还是被剪了,只是一剪子,里面的人和事就都可以去向无踪,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剪片的那天还有人说,其实还可以更锋利。
……
自从有了车再也不用在冬夜里骑行,小军已经逐渐忘记了冬日的寒冷。现在,他像许多人一样里面只穿一件衬衣,常常被杨利民问:
“不冷吗?”
他摇摇头,见杨利民穿着秋衣、羊绒衫、厚外套反而感觉很诧异,其实,不久前他也那样穿,但人就是这样健忘,而且永远感觉别人不可理喻,只有自己才正常。过去和宁远最谈得来,他们一起谈女人、谈未来,也习惯一起谈堕落,那时他们都嫌杨利民滑头、顾奸诈。可现在,一想起宁远,他常常会感觉脊背发凉,和宁远比起来,所有这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显得太小儿科、太微不足道了,宁远不光策划、导演了这一切,连律师也先他们一步请到了,看着宁远客气而遥远的微笑,他常常会有种他们从未谋面的感觉,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曾经相识过,那只能说在某个时刻宁远突然就完成了某种进化,而他们呢,仍旧固执地停留在原地不停张望。因为宁远,顾在他眼里突然变得可爱起来,所以知道杨利民会留下来陪顾,他也没有再生出类似过去的那种不快,反而觉得两个人一唱一和也不错。
没有车之前,小军觉得车比女人重要,不仅仅因为面子,有限的几次从别人车里透过车窗看这个城市的经历,让他感觉到了这个城市不同于往日的柔和,那种柔会瞬间让他心生暖意,觉得这里也可以属于他。而骑着自行车,灯光和冷风从来只会呼呼地从耳边过,那时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到目的地,城市于他而言根本不存在风景,只有灰冷、高大的建筑。骑车那段日子认识女人就会更麻烦些,在校园里骑车带姑娘看夕阳吹风或许是件浪漫的事,但到了大街上,被风那么呼呼吹着,没有丝毫浪漫有的只剩傻气,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姑娘会跟着你一起冒傻气,好几次,他只能把车子先留在公司,陪姑娘吃完饭再坐公交回家,晚一些没有公交的时候,打的钱都快赶上饭钱了。他讨厌和人算计,但更讨厌的还是和钱算计,每次和钱算计都让他心灰意懒,感觉既看不到前路也回不到过去,有的只是无穷尽的延续,而能延续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初有车的日子,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对着外面张望,透过车窗看路边的房子、路边的人、还有那些缩着脖子赶路的骑车大军。看着他们,会有某种类似满足的情绪漫上来,因为除了他别的认都在一瞬间变成了蝼蚁。他不确定之前那些开车的人是否也会像他现在看别人一样看他,看他如蝼蚁般活着,还是会像那些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所谓学者一样,看见蝼蚁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苍生大众写篇研究文章?他只能确定自己不是那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永远都不是,即使有一天他脱离了自己走向另一个轮回,低级趣味也是万万脱不了的,对他而言,那不是一件衣服,那是紧贴着骨头的皮肉。过了一段时间,只是很短的时间后,他就对外面彻底失去了看的兴趣,偶尔有好车和长腿的姑娘闪过,他才会第一时间捕捉到并溜上一眼。
有了车,和所有男人一样他开始想念姑娘。看着满大街那么多的长腿竟然没有一条可以供他触摸的时候,他有些难过,尤其想起宁远被女读者追逐签名的场面,更有想打人的冲动,很想冲过去大喊一声:宁远就是个骗子,骗子。这句话他对张胜说过,当时,正在做记录的张胜抬起头看着他:
“说具体点,时间、地点、经过,慢一点说。”说完低头继续记录,看着张胜,小军说话和找姑娘的欲望都一点点消了下去。
……
她开始翻书。
第一页:
“爱上她,就像月光开出了花……”
第二页:
“我们一生寻觅的不过是一个出口,我们以为只要不断前行,终有一天会与它相遇,却从来没有想过,越走会离它越远,最后,它只是变成我们回忆里的一条路径,一个想象。在水里沉下去的某个瞬间,只有水包裹着我,它是轻柔的又是有力的,只要沉得时间足够久,还可以感觉它包裹着我的呼吸……”
第三页:
“这从来不是离去,也没有人可以真的离去,只是坠入水里,被水不断包裹,离去的方向,我们总以为它很远,在遥远的地方,不是的,现在越来越确定不是的,它很近,就在指尖、手旁边,也许只是一抬手就去了远方……
第四页:
“感觉越来越迷恋水了,但今天却因为她分了心,因为我听到了她的笑声尽管那笑声不是给我的,笑声和她的人一样,都是别人的,但那笑依旧是最好的。只有水可以无尽地包容我,接纳我,因为分心,今天呛了水,最让我难过的是在她的面前。我本来可以一直沉在那里,沉下去……
第五页:
“我感觉离那个出口越来越近了,我可以一直沉着,一直等待着,一直被水包裹着,它抚摸着我的呼吸,还有身体……我知道很快就会到达出口。”
“这是我小舅舅写下的最后的日记。很多天后,一个初秋的下午他最终找到了他认为的那个出口,那天他被水无限包裹着沉入了湖底。他的面庞因为他的出离而永远停留在了最鲜活的时候,在那样一个比花还要灿烂的年纪死去,唯一让人不感伤的就是他将永远不会老去,永远不必担心容颜的衰败,更不必担心世事的变化下,脆弱如人心般反复的折叠,他即使曾经有过煎熬那也是玫瑰花瓣芬芳的煎熬,不会像走过一生的人一样,用沧桑磨砺自己也磨砺别人,直至面目全非,老得连自己都难过,更不会在时光里让自己萎缩变小。因为不必老去他也就妥善地保留了他的体面……文字的下面是一张照片……”
……
这么多年来今晚是第一次连贯地想起连升。她,已经老了。如同书里说的:老得有时连自己都会厌弃,而连升却永远可以年轻着,因为他已经抵达了那个出口,只有她们还在俗世里艰难摸索、爬行。想完连升,先勇说过的话也陆续清晰起来,暗夜里,即使不照镜子,她都能感觉到身体开始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松弛下去,她的肌肉、水分和最好的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一起?在一起能做什么?只会多份回忆的尴尬罢了。
……
梁鸿雁看着窗外缓缓说:
“你看太阳,虽然亮着、还没有落,但是照着已经不暖和了,就像我们,或许从外面看起来没有那么老,似乎还有果肉,其实已经早过了那个季节了,除了连升,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们还有谁能回到四十年前吗?不会了,真的不会了,这世上除了早走一步的连升能安静等候着,我们谁也不能了,就算是煎熬也已经被煎熬习惯了,说到底,我们谁也没有连升那样的勇气,而且,我相信如果连升活着,他也会像我们一样,说到底,勇气只会在某个年纪有,随后就没了,跑得比时间还快。你现在就是头脑发热,而且,你的遗憾里更多的是不甘心,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不甘心总是有念头的不甘心,真的在一起了,你依旧会不甘心,你会觉得一件事开头美好,结局潦倒,而你什么都没有做过,很快就会草草结束,那时,我们或许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留点念想不好吗?”
……
书是宁远托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送过来的,张胜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杨利民,宁远出书后他还没有见过他,倒是领导找他谈了好几次话,让他加大办案效率,还说,不要最后栏目都追踪到下落了,你还没查到。领导最近的一次谈话不但详细询问了案情进展,还看了他的记录,看完记录又抬头看着他说:
“不错,很详细,第一次接案子能写成这样,有前途,图也是自己画的?”他点点头,“不错,挺有想法,好好干。”
每次从领导屋里走出来,张胜都感觉好极了,可以说从来没有那么感觉好过,连大学谈恋爱也没有。只是几句话,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能让他有了被赏识的感觉,因为被赏识又有了想要立刻赴汤蹈火做出一番贡献的冲动。语言这个东西真是太奇妙了,而且,同样的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立刻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如同普通人的手与上帝之手的区别,尤其是你知道他是上帝后,他抚摸你,你等待的是奇迹,而普通人除了为你擦泪顶多是安慰你,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这些鼓励的话,过去或多或少,他也听到过,此刻从一个有破案经验的领导嘴里说出来,它们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含义,除了让他觉得前途一片光明,还感觉到自己干什么都行。那种鼓胀胀的盲目的情绪持续了很久。
在满腔热情的鼓舞下,仅仅为了更了解宁远,过去从不看小说的张胜从拿到书那天起,只要一有空就会捧着看。对于书里出现最多的“出口”两个字,还有对死亡美好描述的字句,最初他有些费解:在书中死似乎不再是艰难的,而是另一双可以带着你自由飞翔的翅膀。里面除了大量的日记,还有宁远回忆母亲、父亲以及与死去的连升对比的描写,相比之下,死去的连升不但保留了容颜、更保留了体面,而他的父亲、母亲却因苍老最终不但丧失了容颜、记忆、还有最初的那份平静。在这之前,张胜还从未如此清晰地思考过衰老,只知道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究竟从何时开始变得面色疲惫,又是何时开始不光棋下得没有他好,还学会了悔棋和唠叨,他不得而知。近几年更是增添很多孩子气,时常需要哄着才能说通。父亲似乎一点点地把他自己最初的样子磨成了平面直至面目模糊。包括现在看个节目都要落泪的习惯,在过去,或者说母亲去世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父亲常常笑话母亲耳朵根子软,随便什么话都信,可现在的父亲竟常常拿着一些小广告,戴着眼镜研究。
他告父亲:“你别看那些,都是假的。”
父亲会很当真地说:“什么假的?又不花钱,你看,这个只是让试一试。”说着还指给他看。他不明白父亲如何会变得这样幼稚,不能想象有一天自己也终将步他的后尘。想到这些,会突然有深深的恐惧袭来,如果真如他今天看到的父亲一样,最终自己就是这样一幅画面,一切都将走向不可思议、走向衰败,那他现在的坚持、打拼又有什么意思呢?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父亲像以往一样浇花,听到身后有响动,头也不抬地说:“快吃饭去,老是不吃早饭可不好,没听电视里说吗?早吃好、午吃饱身体要有多好就多好……快去吃……”说完继续哼着小曲浇花,浸在晨光里的父亲远远望去像油画般有了质感,没有那么不好,更没有那么不堪,活得似乎还蛮有滋味。那刻起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情绪已经开始有了沦陷在书中的倾向,也是那刻起他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丁云凌和宁远一直在一起,那些日记、包括宁远写的文章,她应该在书没有出之前就已经看过了,如果连他这样一个搞侦察工作的大男人都会不自觉受到影响,难道那个女孩儿不会吗?生、死、衰老,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对谁都不会完全陌生,不陌生就容易延展出想象来,看了这本书哪个女孩儿还愿意见证自己容颜的衰老呢?只要看过的人应该都会羡慕连升,都会巴不得变成连升,里面一直描述连升的容貌如何纯净、如何灿烂,他是男人尚且觉得那是一幅美好的画面,何况是女孩儿?也许宁远通过书早就杀死了云凌。书出来后,他详细看了所有新闻和相关的节目,宁远的动机很明显,云凌的消失对新书的上市简直就是最好的炒作,这本书名甚至连父亲都知道,说在棋牌室听人说,去买书送鸡蛋之类的话,回来当新闻一样说给他听。如果云凌没有消失,会有这样的效果吗?云凌是心理医生不假,但毕竟是女人。
……
大学那几年,云凌并没有像多数跨越过高考那道坎的少男少女一样,把憋在体内的荷尔蒙“砰”地一下迅速释放出来,而是像治疗抑郁的文拉法辛胶囊一样,缓慢释放着自己。当然,偶尔,她也会变成那些从踏入大学之门就开始四处寻找爱情的男孩儿们的假想猎物。要知道自己只是假想的猎物并不难,首先从时间上:已经过去两个学年了找女朋友碰壁无数又来找她的,多半只是感觉她更好追,其次是眼神,当男孩儿和她表白连一点儿紧张羞涩都没有的时候,她很确定自己就是那个假想的恋爱对象,她的作用无非是让对方安放他那过量的无处排放的荷尔蒙,如此而已。所以他们镇定,她只有比他们更镇定。那个时候,她并不能确定在爱情里男女持久对峙的究竟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冷静的一方永远可以占上风。
男孩儿在她的冷静里最后通常会变得不再那么冷静。有一个体育系的男孩儿后来竟然因为迷恋她的冷静开始真的追求她,毕业的前一晚,他找到她,没有等她说话就开始狂吻:一切湿热、汹涌、来不及抗拒也来不及思考,他直接触摸的竟然不是她的胸、而是身体和大脑的最深处连接的那个点,那个点一碰,云凌感觉身体里积压的某种东西一下子倾泻而出,后来,她的回应远远比来者还要汹涌还要渴望还要疯狂,那个夜晚,随着多巴胺一再攀升,他们在一个并不偏僻的暗影处完成了身体的交换。他不停说话,她听着,即使是胡言乱语,也带着美妙的音符,他们通过不断重复的简单动作来熟悉彼此的身体同时也了解着自己,夜晚昏暗的夜色像是最好的装饰,也像是最好的礼物。没有了白天刺眼的光照,人用于行走的皮囊连同内心突然就没有了艰涩,仿佛没有了光的阻碍一切才可以变得顺滑无比同时也畅通无阻。一直到很晚,一直到可以依稀看见第二天的曙光他们才逃回宿舍。临走,男孩儿说:
“等我,明天等我。”
那刻男孩儿的眼睛深得像一潭湖水,仿佛只有吞没云凌才能继续踏上明日的归途,云凌看着男孩儿,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脸,耳语般地说:
记住我,一定要记住我。
第二天,不到十二点云凌办完了一切手续然后像逃一样离开了学校。她虽然不是最好的学生,但是所学的内容也都了然于心,关于爱情究竟是怎样的东西,书本解剖得已经很清晰,何况他们还远远不是爱情只是激情,只是不断泛滥的荷尔蒙偶尔找到了一个出口,这种出口或许还可以有很多。爱尚且不会长久,何况激情。尽管多数时候大家总习惯性以为大脑可以控制身体,以为大脑无所不能,以为它是一切的主宰,其实,真实的情形是:身体永远会比大脑早一步,它有它的承受、它的亢奋、它的难过、它的主动、同样也有它的妥协、它的狡黠。而这一切远不是大脑可以随意左右的。它仅仅因为无法一直承受多巴胺的强烈分泌,爱的刺激,就会传递信息使大脑产生疲倦感,所以大脑只好让那些化学成分自然新陈代谢,而这样的过程也许很快,也许很慢,但最多也就持续三四年的样子。随着多巴胺的减少和消失,人不再狂热,一切归于平淡,或者干脆分道扬镳。这就是所谓爱情。那么多人没有因为多巴胺的减少而选择分手,并非是大家嘴里说的像责任、亲情、誓言、承诺这些闪闪发光的词汇,更多的是惯性、是疲惫过后的惯性罢了。但多数时候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作为一个人长久需要的绝不是电光火石一样的激情,而是沉淀在爱情之后的温情,其实,就像母亲所说的,父亲死了,并不是没有可以替代的人,如果,没有父亲留下的那三万块钱她也会很快再找个归宿,找个养家糊口的人,而不会几十年一直飘着。人首先选择的永远是现实,或者说大脑首先选择的永远是现实,而身体总会在某个时刻背离我们。
唯一令她不解甚至佩服的是一直不相信爱情的母亲可以花费人生那么多的时间去寻找去等待爱情,母亲仿佛是一个不相信有金子却时刻在淘金的人一样,不知道该说她有信念还是愚执。反正她不会,既然没有金子,她就不想再用力挖掘,只要不挖掘也就避免了一次次的尘埃洗礼。
在那晚之前她想得很通透,一切的人和事如果没有交集也就没有失望。四年的时间里,除了上课就是找碟片看,她的电脑里下载的爱情片从情色到唯美一样不缺,那样的人生是她有限的人生经验所认为的最安全的人生,她没有想到,只是浅浅一碰,她世界的外壳就会“哗”地碎掉,她规划了四年,而那个男孩儿只需要一个亲吻就让一切坍塌了。她不能确定自己逃离的真正理由,学了四年心理学她已经不可控制地会用潜意识来研究别人也研究自己。她不能确定自己所谓的逃离是因为害怕面对激情退却后的伤感还是根本就没有信心去把握一切。那么没有信心又是来自哪里?仅仅因为自己长相平淡?她那么用力地说“记住我”,是的,最强烈的感觉是——她希望他可以记住她,可以在以后的人生里把她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就像她希望母亲可以把父亲安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一样,不至于混迹于大众。不会像他们毕业前大声朗读的口号一样:“当多巴胺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狂热地爱与被爱着,尽情享受爱的甜蜜;当多巴胺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坦然处之,仍然为爱奉献与努力,不离不弃。”坦然处之是怎样的境界云凌无法想象,在她的人生里只知道,一切太用力的东西都是可疑的,包括十八岁那晚她努力听完母亲的陈述,因为努力所以她的不耐烦显而易见,如果时间足以快乐,它流逝的速度完全可以用光滑来形容,绝对不需要容忍,一旦容忍也就说明了未必快乐。那晚和男孩儿在一起,时间像是溜在冰上,快得不但无法看清甚至无法回忆,只有温热,湿润。那晚更像某个电影片段,在后来云凌的想象里反复出现,但是她永远无法像别的记忆那样进行添加、篡改,她不知道是因为太过短暂所以美丽到无法添加,还是因为没有之前的印象亦没有随后的流逝,有的只是封闭的一小段时间,所以也就无从添加,她更不知道他是否会像她希望的那样,认为她特别,所以会安放在一个特殊的角落给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他们永远不用经历容忍、经历失望,也就避免了面对残渣时需要拥有的坦然处之。
很多年后,她也想过,如果他一定要找她,即使她逃离般先走了,只要努力找应该可以找得到她。
她开始换个角度回想那段记忆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年,诊所也终于在第二年夏天来临前安上了空调。前一年的整个夏天,当她的病人喋喋不休叙述陈年旧事的时候,摆在病人旁边的电风扇就那么一直摆来摆去,对于病人尽管不会有悲悯和探究的心情,但也不至于厌烦,毕竟受过专业训练,而且对于她来说这就是份工作,工作需要的是尽责而不是感情。但是,那个夏天她却受不了电风扇的摇摆,而且是那种固定格式的摇摆,风扇头转过来转过去,点一下再点一下,不多一秒也不少一秒,她发现病人反而并没有像她这样的焦虑,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电风扇仿佛像诊所的桌子、椅子、墙面一样可以和整个诊室融为一体。而她每次看着它摇摆,过半小时后就会有一种冲过去想抽它一顿的冲动,她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可笑,尽量控制着自己焦虑的情绪,但整个夏天还是被扰得心烦意乱,所以没有病人光顾的下午,即使再热她也不会开风扇,她甚至想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把风扇直接从二楼扔下去,当然,一切只是想想而已她没有那样做,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她知道情绪的管理对于她们这个职业来说有多重要,任何一次情绪的公开崩溃都有可能葬送整个职业生涯,所以一切的一切只能在脑子里完成,从雏形到成型到碎片自我生成再自我消化,仅此而已。她甚至不如她的那些病人,他们至少可以向她倾诉,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经历,曾经想过要这样要那样。其实她也知道自己怎么能和他们比呢?很多时候不得不说钱是个好东西,至少它可以让你短暂安稳,哪怕只是释放情绪,这个世界上有时连倾诉都是奢侈的,向她倾诉,她付出的是时间、是专业的知识,而他们付出是钱币,用以物换物的理论来说,很难说谁帮助了谁,谁又成全了谁。
夏天过后电风扇像以往一样被搁置在诊室靠窗户拐角的地方,因为电风扇比她来这个诊室的时间要长,所以尽管她不喜欢、尽管看着闹心却仍旧遵循了一条在诊所谁都不说却早就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任何人、任何物都是有先来后到的,而且已经既定的或是摆好的位置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谁都不会去轻易更改。因为大家都是干这一行的,很容易通过一些细微的小事揣测出你真实的心理,任何的释放如果不够安全那云凌宁可选择搁置,因为事后一系列的揣测会让你更加不安。上班两年云凌已经开始逐渐按着大家的规则行事、度日,也许不够自由但看着周围每个人都这样生活这样习惯着,云凌的心也日趋平静,但只是平静,她明白那不是安稳。
安上空调的第二天,她的老板林金生在第一时间把电风扇拿回了家。林金生长了一张油腻腻的脸,身体也略显笨重,但做事却一反常态地干练,只要够细心从他的眼神里可以很容易读到精明甚至是狡黠。云凌曾经深入地琢磨过人的长相,很奇怪,从小就听人常说貌如其人的例子少之又少,反而多数的人都长了一张和内心极不相符的脸。看着外貌平淡往往掩藏着深刻的激情,看着宽大、肥腻的身躯包裹着的是一颗精细敏感的灵魂,有的看起来美艳至极、风情万种,内心却心如死灰,无爱亦无恨,而那些看似平庸老实的长相里很多时候亦藏了太多不堪和污浊。仿佛上天是故意为了某种平衡而设置一般。就像林老板,如果没有那样肥壮的身躯,他的精明永远一目了然,那该多令人担心甚至是讨厌的一件事,有了身躯的包裹、遮掩,一切都顺滑了许多,就像自己,或许因为热情本质上只是如同被水滴包裹着,一碰就会破,所以才要时刻戴上一副冷静、淡定的面孔,否则,热情随处四溢的局面同样也是令人担心的。同事形容云凌总说她柔和、淡定,有的是对病人的耐心,却丝毫可以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还说,想象不出她这样的人谈恋爱会是怎样一副模样。云凌听到同事这样说,总是抿嘴笑一笑,很多年前,从和母亲谈父亲无果的那个夜晚起,云凌已经对谈话、思考、解释以及共鸣之类形而上的东西望而却步,能懂最好,不懂也罢,总之不会更多地去解释,因为她太了解人心感兴趣的点能碰上的几率真的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解释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但是,一旦开启了解释的模式,心也就永远不会安宁,你会开始期待对方的回应,人世间的事情一旦需要回应、需要交集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扯皮里……那是一场持久战,比的不是对错而是谁更有耐心。
……
作者简介:
李燕蓉,女,山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就读于鲁院第十八期高研班。
年就职于晋中市文联,从事《乡土文学》美编工作年开始写小说。发表近80多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钟山》、《山花》、《山西文学》、《黄河》等杂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曾参加年全国青创会;年《飘红》获第五届“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年中篇小说集《那与那之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年小说《出口》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新人奖”。年小说《出口》获第七届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白烨:故事里的心事
——读李燕蓉长篇小说《出口》
李燕蓉自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以来,一直以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主,所北京哪家正规医院治疗白癜风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医院在哪